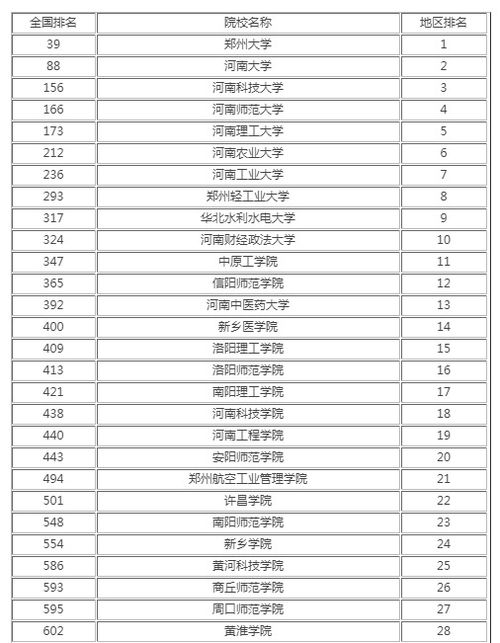李公明|一周书记:成为历史事件的出版业及其……光辉时刻
2023-01-20 22:05来源:网络本地 0人已围观
摘要《印刷中的革命:1775-1800年的法国出版业》,[美]罗伯特·达恩顿 / [法]丹尼尔·罗什著,汪珍珠译,上海教...

《印刷中的革命:1775-1800年的法国出版业》,[美]罗伯特·达恩顿 / [法]丹尼尔·罗什著,汪珍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11月版,424页,78.00元
1989年2月18日至4月29日在纽约公共图书馆(NYPL)的D. Samuel和Jeane H. Gottesman展厅举办了题为“印刷中的革命:1789年的法国”的展览,以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特邀策展人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和巴黎大学教授、著名的18世纪文化史学者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展览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由罗伯特·达恩顿和丹尼尔·罗什主编的《印刷中的革命:1775-1800年的法国出版业》(原书名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1775—180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9;汪珍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11月)。其实在主展览及专著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成果,除了向走进展场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图文观赏机会之外,还延展到在尚伯克(Schomburg)黑人文化研究中心和表演艺术研究中心的音乐和舞蹈区都举办了相关展览,一系列公共项目也开展起来,最后还与美国图书馆联合会联合在各大城市图书馆举办了巡回展。更为潜在的重要影响是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大革命时期法国文化史研究的兴趣,直到今天它所激发的问题意识仍然在相关研究议题中延伸。
不妨先回到1989年世界各国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文化活动中去,或许更能理解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这个展览所具有的独特意义。该年7月14日,在巴黎协和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大革命二百周年官方庆典活动。有学者在一个多月后认为,“协和广场上的表演,典型地说明了这场官方二百周年庆典未公开宣布的主题:‘大革命结束了。’……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将被晾在一边,1989年的主角是孔多塞:学者、哲人、改革家、‘温和的’革命者,以及他未能使之完美并予以控制的大革命的受害者。……但大革命依然是含混、复杂和具有颠覆性的,即便两百年后,它仍然是难以驯服的。”“事实上,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重新开启了激越的史学争论,这些围绕着革命的意义而展开的争论,自革命发生之日起就已开始。《巴黎革命报》(Révolutions de Paris )是最早的且阅读最为广泛的报纸之一,在塑造革命意识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早在1789年9月,其读者就要求能从中看到‘自首次显贵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以来在法国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历史和政治画面’,以便为解释‘这场刚刚发生的令人惊异的革命’的性质提供方法。”(罗杰·夏蒂埃《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凯斯·米歇尔·贝克尔、斯蒂文·劳伦斯·卡普兰“原编者序”,1989年8月26日;洪庆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4-5页)作者在谈到重新开启的围绕革命的意义展开史学争论的时候,马上就切入当时发行的报纸与读者的需求及其目的,这仿佛是几个月前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办的展览的回响。
罗伯特·达恩顿在1989年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就认为,虽然“印刷在法国大革命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也曾引起过讨论,但还从来没被认真研究过。(《印刷中的革命:1775-1800年的法国出版业》,导论,第1页)。他说这话是有依据的。因为他从1964年就开始从事这项研究,当时他还是研究生,研究专题是法国大革命前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就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他查阅了大量未编目录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小册子。在1979年出版的《启蒙运动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80,1979;叶桐、顾杭译,三联书店,2005年)中,已经谈到在大革命的前两年里有大约三百五十种报纸在巴黎骤然出现,把旧制度上流社会的报刊挤出了市场;新冒出来大约两百家印刷工场彻底改变了巴黎的印刷业,“那些没有特许权的粗野之辈接掌了新闻业,把审查制度和特许权抛进了时代的潮流当中,并且把公众所需要的东西交给他们——不是书籍,而是政治小册子和报纸”(529-530页)。同时他还指出历史学家对于政治的兴趣并没有使他们对出版业的革命给予过多少关注,并且对不可能在这里充分讨论这个问题感到遗憾。十年以后的这个展览和主编这部书完成了他的心愿。
早在1930年代,法国文学批评家、《法兰西文学史》杂志主编丹尼埃尔·莫尔内(Daniel Mornet,1878-1954)就开始研究大革命前的图书出版与阅读问题。他的名著《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 1715-1787,1933)的第十章就把“报刊”和“教育”作为研究专题,并且把两者的关系及意义讲得比较清楚:“对于那些在法国印刷的报纸,它们的主持者(当时称‘创办者’)和印刷商几乎难以逃脱政府的严厉措施,如果它们胆敢让政府不悦的话。所以各家报纸必须极端谨慎。这种谨慎在教育中更为必要,因为所有教师都可能被辞退。但正是这种谨慎以及教育中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使得受到严密监控的报刊和中学教育中的任何变革都显得更为重要。另外,即使这些变革不是很深刻,它们也会通过其传播而具有重要意义。报刊和教育是传播新思想的最主要的两种途径。”(《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144页) 达恩顿在1996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1996)中指出是丹尼埃尔·莫尔内首次提出了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在阅读什么的问题,并以此为起点探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他认为无论莫尔内的答案是否站得住脚,但他提出的问题还是成立的。“他的问题启发了后来的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进行四分之三世纪之久,尝试确认法国人在旧政权统治时期都阅读哪些文学作品。”(《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其实早在达恩顿之前,莫尔内以思想起源作为大革命动因的这种研究视角在1991年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研究中就既被作为一种不应抛弃的遗产,同时又不断把它作为质疑的对象;在这种学术系谱的清理中自然要把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76年的《旧制度》也纳入进来,指出他们三人的共同观点是阅读能够改变读者、书籍制造了革命。他进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反拨:“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革命‘制造’了书籍,而不是相反,因为正是革命赋予某些著作先驱性和纲领性的意义,将这些著作构建为它的起源。”(罗杰·夏蒂埃《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991;洪庆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83页)不过这种“革命对启蒙的这种回溯性的重构”的反拨似乎有点过头了,于是接下来的阐释也带有修正的意味:我们不妨这样表述:在旧制度末期法国的思想和情感转变中,印刷物的传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位置?除“哲学书籍”大规模呈现出的批判性和谴责性的表象之外,更应该强调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阅读方式的那些变化。新的阅读风格的新特征是:数量更多、阅览时间更少的文本,灵活易变的和个人化的阅读方式,阅读失去了所承载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人们对书籍的态度是更自由、更随意和更具批判性的阅读方式。(84页)达恩顿的说法则是:“历史学者通常认为印刷品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一种记录,而忽视了印刷品伴随事件一起发生,本身就是事件的一部分。”(《印刷中的革命:1775—1800年的法国出版业》,导论,第1页)我相信把印刷出版业的变化作为大革命历史事件的一部分,重点考察其间关键的光辉时刻与深远影响,可以跳出“书籍与革命”的起源争辩,把目光聚集在作为历史事件的出版业的内在变化。
现在可以回到《印刷中的革命:1775-1800年的法国出版业》。达恩顿撰写的“导论”部分非常精炼地概括了该书的核心议题和各部分内容:“本书要直面的问题是:印刷在法国大革命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们希望通过考察印刷业,为从整体上研究法国大革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个问题也很直观:“没有印刷机,他们能攻陷巴士底狱,但无法推翻旧制度。为了夺权,他们必须争夺言词并广泛传播之,他们在报刊、历书、宣传册、招贴报、图片、歌单、信纸、棋盘、配给卡、钱币等上面印制能够传达某种信息的内容,并将其植入2600万法国人民的头脑中,这些法国人民中有很多正困顿于贫穷和压迫,很多深陷于茫然无知,很多则无法阅读关于他们自身权利的宣言。”这是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关于舆论与革命的关系:为了夺权,先做舆论。但是在主流历史叙事中,舆论的出现及传播并非总是被看作是一种创造性力量。因此,“本书的期望就是要重新唤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重新认识印刷出版的力量”(导论,第1页)。由此引出的既是专业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指向了“那些改变所有人生活的力量”,例如,出版自由在其诞生之初有什么必需条件?对于读者、作者、出版商、书商和以印刷业为生的人来说,出版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1789年7月14日以后,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印制任何材料,包括在新的掌权者看来具有煽动性、诽谤性或色情的内容?印刷机在革命政府的条件下如何运作?其产品深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程度又有多深?……正是这些改变世界、改变人民生活的力量塑造了印刷出版史上的光辉时刻,作者希望在该书能够“捕捉到了印刷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刻”。
该书第一部分“革命前形势”描述的是旧制度下的出版业,关键词是在旧政治体制下的严格管控、地下出版业的兴盛和意识形态的斗争。第二部分“印刷中的革命”考察法国大革命如何影响出版商、印刷商和书商们做生意的方式,核心是旧的出版体制的崩溃与新体制的建立,许多问题过去未被考察。第三部分“印刷品”在图书和报刊之外还讨论了其他各种印刷材料和传播媒介,如印刷如何与歌曲等媒介交集,诸如历书、信纸、扑克牌、棋盘、纸币等日用印刷品如何将革命讯息传入日常生活领域。在我看来这一部分就是关于出版业如何成为传递革命信息的毛细血管,是最贴近日常生活的舆论史。
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紧贴大革命前法国的言论与出版自由问题,史料极为生动、丰富。丹尼尔·罗什在《审查与出版业》中开头就说很难相信在十六世纪至法国大革命爆发,对言论和写作的审查在法国居然是一项官方政令,“思想警察”的存在竟然是一种常态。尽管很难相信,但是他的研究把这套审查与监控体系剖析得非常深入。“旧制度时期,根本就没有出版自由,因为王室自掌权以来就对印刷商和书商进行监视,并形成了控制思想传播的机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各种手段无所不有……。”(第7页)整个机制大体上是双轨并进:一是预防性审查,每本书的文稿内容在出版前都必须受审查;二是禁止地下印刷品的秘密交易,“清楚显示了专制主义国家及其统治者对印刷品的重要性有着非常强烈的意识。他们也看到印刷品是知识和思想的主要载体、所有政治和宗教讨论的媒介、颠覆性批评的表述工具,同时也可以是知识分子表达顺从和默许的工具”(同上)。但是整个体系的运转并不总是很成功,禁书的传播还是难以阻止,而审查员和图书警察一时镇压一时容忍,日子也不好过。某些著作不许出版,也需要说明理由。随着经济发展的转型,出版审查就要在意识形态管控与繁荣出版商业之间摇摆。在1750-1763年担任法国图书业主管的马勒泽布(G. L. de Malesherbes)成了君主制下出版监控模棱两可政策的象征。他既是具备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哲学之友,同时又是专家治国主义威权的代表,因此他一方面以专制权力划定了维护宗教与政治正统的不得超越的红线,另一方面为保证禁令有效而尽可能缩小禁止的范围。“他的观点就是,审查制只有在理性范围内获得各方面人群的容忍和接受才能成功”。(13页)但是这种开明的出版专制策略在1750年之后实施起来越发困难,因为禁书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划清,君主制的堡垒(学院和审查机构)也受到了新观念党派的四面围堵。
在大革命前夕,法国有一百六十多名审查员受雇于国家。而图书的作者们也逐渐养成了拜访审查员和适应审查员要求的习惯,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都曾去拜访文化官员和审查员。
这些审查员都是从特权和精英这样的阶层中招募的,同样具有矛盾性:既要维护专制政治,又希望容忍程度合理的新观点。因此允许作者与审查员之间的协商、彼此退让和不同等级的出版许可。既要禁止某些图书出版,但是又不能太过明显违背国家公开宣称的原则——鼓励出版业的发展和“国家应该尽可能少发禁令”。另外,在审查员的审读报告中还可以看出私人关系的存在。(19页)审查员皮盖(Piquet)对《新爱洛依丝》(Nouvelle Héloïse)的文本审查很有意思:他进行了二十三处修改,其中二十一处是语言上的细微修正,“以消除可能引起麻烦的弦外之音,另两处则需要完全删改某些段落,因为这些段落公然质疑教会和国王的威权”(21页)。
图书警察则扮演了另外一种角色。他们针对的是那些在合法出版业与秘密出版业之间的模糊地带游走斡旋的文化人,有些是想赚快钱的书商和印刷商,也有分销人、小贩、小商人,以及带薪作家和自由文人,所有这些人都受到监视。监控从生产环节开始,警方要对所有印刷机和字模之类的印刷设备进行登记,禁止地下印刷作坊的运作;对已获执照的印刷坊的工作进行日常检查;对进入王国范围及其主要城市的所有图书开箱检查。但是这套体系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期就漏洞百出,反而还促成了禁书需求。正如狄德罗在《有关书店贸易的信》中所说的,“禁止得越厉害,被禁作品的价格就抬得越高,就越加吸引人们想读,购买的人就越多,阅读的人也就越多”。书商一旦制度某书被禁,马上就会说“很好,再印一版!” 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在1659年至1789年之间,大约有千名违法者因触犯图书生意的相关法规而被押送巴士底狱,这个数字大约占巴士底狱所有囚犯的百分之十七。当然大鱼们往往漏网,他们有些受到高层的保护,有些则是身处国外而比较安全。
丹尼尔·罗什最后告诉读者,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终结图书警察制和审查制。《人权宣言》既振聋发聩地宣告“自由交流思想与意见乃是人类最为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言论、著作与出版”。同时认为“但应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此项自由的滥用承担责任”,使不容忍这种自由的可能性合法化。“情况同样岌岌可危,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自由原来如此脆弱不堪。”(32页)
在第二部分“印刷中的革命”,卡拉·赫西在《出版业的经济剧变》中继续追问在大革命之后“出版自由在实践上到底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她指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不仅因为它将启蒙思想从旧制度的监督管辖中解放了出来,还因为它将‘启蒙’从一种思想转化成了一套新的文化实践,这套文化实践的基础就在于最自由、最广泛的思想上的公共交流。定期出版的和短时效的印刷品,较之于图书,更好地服务于此目的。”这种转变的实质就是出版与阅读的民主化,“也就意味着在思想的公共交流上允许更广泛的社会主动性和参与度”。(114页)菲利普·米纳尔在《工人的骚动》一文中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民主化的趋势:“尽管传统书商因为这些短时效出版物的增长而遭受巨创,但大革命这几年,一种新的对文字的敏感却越来越成熟了。人民希望获得资讯。出版自由一下子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方式和表达。”(125页) 另一个例子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印刷品中,容易被研究者忽视的是新政权发布的通告、政令一类印刷品的生产与传播过程。皮埃尔·卡塞勒的《印刷商与市政》就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旧制度下,市政当局的审议记录从来不会让大众得知,唯一以印刷品出现的文本就是以传单或布告形式颁发的法令。革命后的政权则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专门负责大会议程的编辑及印刷和出版,让大众知情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因此市政府在革命期间的印刷工作要求印刷商时刻准备以应对各种紧急任务,1789年到1791年期间市议会的会议议程全都被印制了出来。(118页)出版自由在这里的意味有了些许变化—— 鉴于公众的知情权,政府没有不出版的自由。这也是出版民主化的应有含义。
比报道会议议程更为激进的民主化是通过报刊对会议内容和出席代表进行评议和批判。
杰里米·波普金的《报纸:新闻的新面孔》(收入第三部分)以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激进报刊、马拉的《人民之友》为例,说明“对于马拉来说,描述国民议会会议的目的不是要提供无党派倾向的会议记录,或是引导大会中爱国主义成员的想法与公众的想法形成共同的目标,而是要公开和揭露代表们谋逆的意图,动员人民反抗他们,就像他在其报刊中所做的慷慨激昂的反抗”(187-189页)。这是新闻媒体介入政治和事件的更为激进的方式,无论这种介入正确与否,它都表明新闻媒体对议政与立法政治肩负的权利与责任。当时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卢韦(J.B.Louvet)议员(其本人也是一名新闻人)谴责并警告这种现象,因为担心新闻媒体“这个永久的革命煽动者”如不加以控制,会动摇民众对政府的共识。波普金认为,“法国革命者是第一批面对代议制政府下新闻自由所固有之悖论的人: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代表,但他们喜欢的并不一定是代表本身的形象,而是媒体所打造的形象。在革命时代,是拿破仑最终解决了政治家与新闻人之间的死结,他把两者都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189-190页)。或许也可以说,拿破仑是最早读懂了喉舌论的法国人。
在大革命时期传播的政治小册子中,有不少是以戏谑、辱骂、诽谤的文字以及以色情想象作为攻击性修辞的作品。安托万·德·巴克的《小册子:诽谤与政治神话》就专门讨论了自1789年至1792年的政治色情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的作者不详,言谈粗俗下流,“但在其粗鄙恶劣的表面之下还隐藏着描绘政治人物时的微妙之处。这种自成一体的作品有助于我们开始从整个范畴来理解革命小册子的方法论”(194页)。虽然以色情话语攻击教士和贵族在大革命前就常见,但是政治性紧张的程度却前所未有。在1789年之后,对名人的色情攻击随着形势的发展迅速增多。这些作品虽然淫秽下流,但对政治发展都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其目的就是利用性轰动效应来证明旧的统治阶级根本不适合新时代,贵族在道德上的败坏与肉体的放荡紧密地交织到了一起,吃瓜的巴黎群众对这类文字的态度也越来越坦然。
大革命时期印刷出版的年历既反映了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节奏在激进动荡的革命潮流中所具有的保守性,同时也反映了激进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尤其是后者,在我印象中这个问题在年历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尽管我们一直强调以“大众化”与“普及性”反对文化上的精英主义。利斯·安德里在《年历:革命化传统文类》中认为,通过研究可以得到一个印象,就是大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常生活的节奏;另外,历法改革虽然时间不长,但其重大意义是对于大革命创造的旧制度这个概念,把时间区分为前、后之别。因此,我们要重视以年历为中介来重构时间的疯狂野心。(257页)
第三部分的最后三篇论文是罗尔夫·雷夏尔德的《版画:巴士底狱的形象》、劳拉·梅森《歌曲:混合媒体》和詹姆斯·利思的《短时效印刷品:以意象进行公民教育》,构成了从绘画、音乐到日用品美术设计的艺术生产的三种媒介和传播面向,正是革命时期艺术史的重要内容。雷夏尔德的论文以大革命时期的以单面全版的形式印刷的政治版画为研究中心,指出“对图像再现的强调使得这种印刷品对大革命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首先它们帮助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大革命的政治进程和激进化成为可能。……不仅让人们获得了革命信息,而且将普通人拉进一个在越来越广阔的公共领域里交流和形成观点的进程当中,并且是朝着民主化的趋势发展的”(259页)。作者以极为丰富的版画作品和细致深入的图像阐释揭示了图像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而且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本身,是事件与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指出过去大革命史学家只满足于使用几幅事件型版画来例证其叙述,“只有到最近,我们才开始认识到,作为历史学资料的革命版画的真正和独特价值并不在于其对个人或事件的描述,而在于其对当时集体性观点和问题的象征性、隐喻性和类比性阐释。它们可以向我们展示时人处理和阐释其经历的方式——在文字资料中仍被掩藏的方式”(261页)。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与结论把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与历史图像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为历史图像学的学科建构提供了异常出色的研究案例和方法论启示。
劳拉·梅森关于1792年的革命歌曲《马赛曲》与反对雅各宾恐怖的歌曲《人民的觉醒》(Réveil du peuple)这两首歌的矛盾冲突及其意义的论述非常有意义。作者指出,重要的问题不是哪首歌词更能代表大革命的理想,而是每首歌被演唱时的情境。《马赛曲》被捍卫是因为它曾经送共和国的军队走向胜利,但是当恐怖时期的断头台正在疯狂地运转的时候,它被攻击是必然的;而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人民的觉醒》代表了人民反对血腥暴政的心声:
“法兰西人民,兄弟们,/ 你们看到,难道不会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吗?/……什么!这群吃人的暴徒,/ 地狱从肠子里呕吐出来的暴徒,/ 鼓吹着屠杀和血流遍野!要用你的鲜血去淹没!”(303页)这两首歌曲在演唱中产生的冲突又成为媒体报道与争论的事件,歌曲、演唱以及与媒体文本之间的变化关系正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大革命中的文化实验与斗争的复杂性。“巴黎民众与国家政府之间从恐怖时期中期开始就日益增宽的政治鸿沟,在《马赛曲》与《人民的觉醒》争端和之后的沉默中找到了其文化体现。巴黎人不得不等到19世纪才再次发声。”(308页)作者指的应该就是1830年的七月革命,巴黎市民以起义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以他创作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向七月革命和永恒的自由之神致敬。

Tags:
相关文章
随便看看

刘亦菲个人资料介绍(刘亦菲惊艳全部照片
#如果时光倒流,你会做些什么#...
福建学校人数排名前十(福建科举人数排名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福建省的高中教育已经迈入了新的阶段。近年来...
海带怎么凉拌好吃,海带是一种营养丰富、
材料: 海带:适量 蒜末:适量 青红辣椒:适量 醋:适量 生抽:适量 糖:适量...
定位标签贴膜怎么用,1. 选择合适的定位标
1. 选择合适的定位标签贴膜 您需要选择合适的定位标签贴膜。通常,定位标签...
2025至2029连续5年没大年三十吗 2025至2029为
我们把大年初一的前一天,也就是旧的农历年最后一天叫做除夕,在除夕这天,...
家里马陆虫怎么彻底消灭
2. 清除环境:马陆虫喜欢潮湿的环境,所以首先要尽量保持家里干燥。定期清理...
夏塔瓦神庙最后怎么上去,夏塔瓦神庙是印
夏塔瓦神庙是印度古代著名的宗教建筑之一,位于印度马哈巴莱什瓦尔邦的奥里...
拉萨到林芝怎么去
拉萨到林芝最常用的交通方式是乘坐长途汽车,从拉萨东郊客运站出发,经过...
点击排行
 西门子洗碗机如何使用
西门子洗碗机如何使用